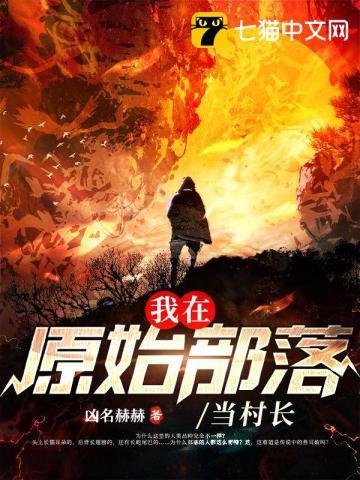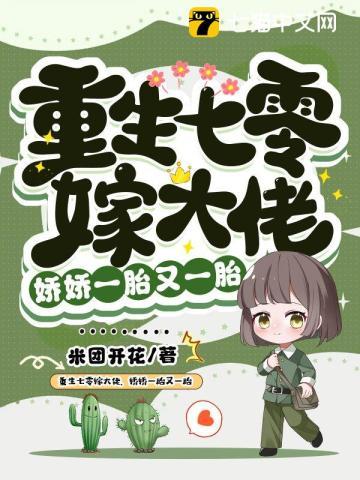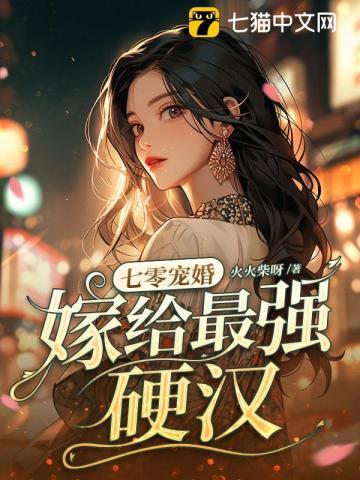章太炎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小说巴士★https://www.xs84.co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依我看来,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,如兼叙多人多事,就非骈体不能提纲。
以《礼记》而论,同是周公所著,但《周礼》用骈体,《仪礼》却用散体,这因事实上非如此不可的。
《仪礼》中说的是起居跪拜之节,要想用骈也无从下手。
更如孔子著《易经》用骈,著《春秋》就用散,也是一理。
实在,散、骈各有专用,可并存而不能偏废。
凡列举纲目的以用骈为醒目,譬如我讲演“国学”
列举各项子目,也便是骈体。
秦汉以后,若司马相如、邹阳、枚乘等的骈文,了然可明白。
他们用以序叙繁杂的事,的确是不错。
后来诏诰都用四六,判案亦有用四六的(唐宋之间,有《龙筋凤髓判》),这真是太无谓了。
凡称之为诗,都要有韵,有韵方能传达情感。
现在白话诗不用韵,即使也有美感,只应归入散文,不必算诗。
日本和尚娶妻食肉,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,何必称做和尚呢?诗何以要有韵呢?这是自然的趋势。
诗歌本来脱口而出,自有天然的风韵,这种韵,可达那神妙的意思。
你看,动物中不能言语,它们专以优美的声调传达彼等的感情,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。
“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咏,律和声”
这几句话,是大家知道的。
我们仔细讲起来,也证明诗是必要韵的。
我们更看现今戏子所唱的二黄西皮,文理上很不通,但彼等也因有韵的原故。
白话记述,古时素来有的,《尚书》的诏诰全是当时的白话,汉代的手诏,差不多亦是当时的白话,经史所载更多照实写出的《尚书?顾命篇》有“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”
一语,从前都没能解这两个“肄”
字的用意,到清代江艮庭始说明多一肄字,乃直写当时病人垂危舌本强大的口吻。
《汉书》记周昌“臣期期不奉诏”
、“臣期期知其不可”
等语,两“期期”
字也是直写周昌口吃。
但现在的白话文只是使人易解,能曲传真相却也未必。
“语录”
皆白话体,原始自佛家,宋代名儒如二程、朱、陆亦皆有语录,但二程为河南人,朱子福建人,陆象山江西人,如果各传真相,应所纪各异,何以语录皆同一体例呢?我尝说,假如李石曾、蔡孑民、吴稚晖三先生会谈,而令人笔录,则李讲官话,蔡讲绍兴话,吴讲无锡话,便应大不相同,但记成白话文却又一样。
所以说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,亦未必是确实的。